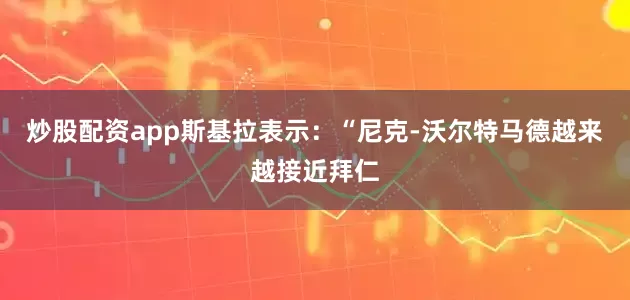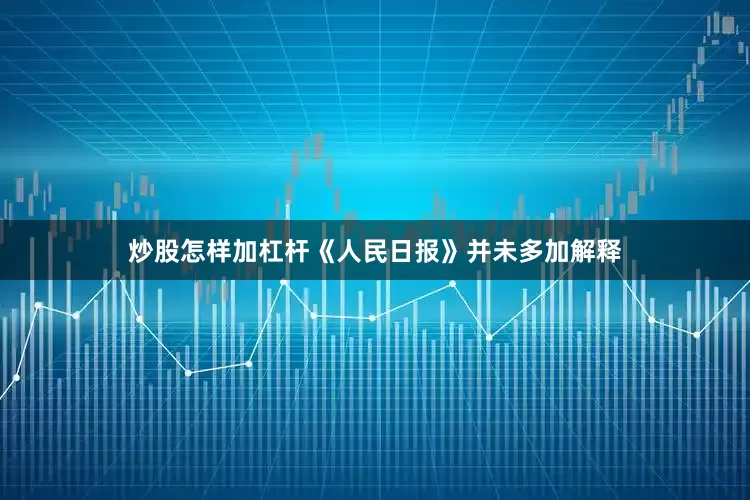
1969年3月的乌苏里江还没完全开冻,中苏边境炮声震耳。那一次珍宝岛交火成为毛主席重新审视国际格局的分水岭。对岸的枪炮提醒北京:必须寻找新的战略支点,于是视线悄悄越过太平洋,落在了白宫里那个善于运用“沉默多数”的美国总统身上——理查德·尼克松。
一年后,毛主席安排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,“四人合影”刊出,《人民日报》并未多加解释。对于研究东方式含蓄的美国情报官而言,这无异于晦涩的摩斯密码。尼克松却被照片勾起好奇,他揣测那是“邀请函”,于是默许基辛格展开秘密探路。

1971年7月9日傍晚,基辛格乘巴基斯坦政府飞机抵达北京郊区的南苑机场。周总理与他谈至深夜。基辛格后来在备忘录里写下短句——“他们愿意谈,甚至愿意吵,但绝不愿意沉默”。从此,中美关系像拧紧的发条开始运转。
1972年2月21日中午,机舱门打开,寒风灌进“空军一号”。尼克松走下舷梯,先把手插进口袋暖了两秒才伸向周总理。那一握,被无数闪光灯定格。三小时后,基辛格按预案问:“主席是否已经休息?”得到答复“请他进来”。

尼克松推门时,毛主席正挨着木质书架坐着,桌上几片茶叶漂浮。见面第一句话竟是:“选举那年,我投了你一票。”翻译将句子送到尼克松耳里,他心里一阵发热——这是肯定也是调侃,足够当冰breaker。
原定十五分钟,被两人聊成七十分钟。期间,尼克松突然提出:“能否留下主席的墨宝?在我们国家,这象征非凡友谊。”毛主席手一摆,让工作人员递来笺纸。没有楷书、没有诗词,他挥笔写下十二个字:老头坐凳、嫦娥奔月、走马观花。写毕微笑:“就这样吧。”对方连连道谢,却摸不着头脑。
回到钓鱼台,白宫随行人员围着纸条发表意见。有人猜是古典典籍,有人查辞典,一夜无果。消息传回华盛顿,史学家、汉学家、财经顾问都尝试破译。可这十二字既无典故,又缺语法线索,像谜语却又不像谜语。尼克松干脆把题字锁进椭圆形办公室的保险柜里,免得旁人看笑话。

几个月后,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报告把“三个成语”拆成多组含义:一说“老头坐凳”暗指美苏老迈互相钳制;一说“嫦娥奔月”影射阿波罗计划;一说“走马观花”提醒美国代表团行程匆匆。有意思的是,哪一种解释都能自圆其说,却都不能自证其对。尼克松在回忆录里干脆写下:“我宁可相信毛泽东以最朴素的方式,记录一次偶遇。”
1974年春,毛主席在武汉与地方干部谈话,无意间提起此事。他笑道:“美国朋友想复杂了,那几句没别的意思。坐凳就是坐凳,上月就是上月,走马就是走马。”旁人听罢莞尔。

毛主席的低调坦率,其实贴合了当时的策略。那年他已81岁,肺气肿反复,可精神头儿仍在。他知道,中美之间隔着文化与制度的峡谷,一纸白话远胜晦涩暗语。把大事讲得干净利落,省时省力,也省得对方疑神疑鬼。
题字轶事之外,礼物交换同样精彩。美方送来瓷塑天鹅、麝香牛、加州红杉幼苗;中方回赠大型绘画《千里江山》复制品、景泰蓝大花瓶,外加两只活生生的大熊猫。“玲玲”和“兴兴”抵达华盛顿史密森学会那天,数万市民排队三小时只为一瞥国宝。有人开玩笑:“这可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外交信使。”
然而最让尼克松念念不忘的并非熊猫,而是那包四两重的“大红袍”。周总理说明来历:岩壁仅剩三株母树,每年采摘不及半斤,主席分走一半,又剥出一半送你。“相当于送了半壁江山。”尼克松这才明白自己捧着的是什么分量。

同一年,基辛格在东京遇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,后者羡慕美国捧回茗茶。基辛格把手比成指尖:“只有这么多。”外相大笑:“越少越贵,懂了。”
1976年2月21日,尼克松再度踏上北京。身份已经转换,礼遇却丝毫未减。毛主席脸庞浮现红晕,举杯以水代酒:“君子之交淡如水。”尼克松迟疑两秒,举杯回应。对话持续一小时四十分钟,内容未留文字记录。随行译员唐闻生只说了一句:“两位老人都很高兴。”

12个字的纸条至今仍收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,外界偶尔申请查看。懂汉语的人看一眼就能读通,可故事的筋骨只有当事人心里最清楚。它记下一个特别年代:冷战棋局突生变线,因两位决策者的互释善意而转向。
对大多数旁观者而言,题字像谜,却更像指针——指向沟通、指向务实、指向打破成见。毛主席没用纵横捭阖的典故,只写生活化的三个镜头,让外交场合一扫玄奥。简单二字,恰是难得的精妙。
牛股配资网登录入口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专业炒股投资此时以夜尿量增加为其特点
- 下一篇:没有了